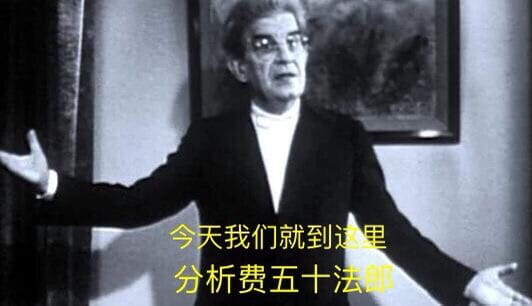《斜目而视》是左翼的网红哲学家齐泽克写的一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他用电影做例子,试图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讲解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当然,他讲的电影我是几乎一部都没看过,以至于这本书的初衷——通过电影用通俗的方式看哲学——一下子就反了过来,变成了通过哲学用狗都不看的方法云电影……
好在这本书的最后还有季广茂写的译者后记,这个后记比起原文而言好读了许多(尽管原文已经够好读的了),至少相当适合中国人去理解——因为他的例子都是什么“莫道石人一只眼”啊三毛啊之类的,还是比齐泽克那堆希区柯克好懂一点的 。
现实感
当我们遇到一些创伤性的事件时,我们的现实感就会破灭,我们不敢相信面前的事情是现实,以至于要掐自己一把确认是不是在做梦。
我们对于现实有一种完整的和谐的现实感,是因为我们把一些创伤性的、无法理解的事情,通通排除在现实之外;就好像一座干净的都市把粪便通通排到下水道里去一样,现实感才得以成立。如果不幸哪一天马桶堵了,大便溢得满屋子都是,我们就会立即丧失现实感。
现实感之所以成为现实感,就在于大便一样的实在界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梦境的意义
在梦中我们遭遇了自己的“欲望之实在界”,明白自己的真实欲望。我们自以为是个好人,但是在梦中我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就要被依法执行了,这才从梦中醒来。于是自我安慰:太阳照常升起又是新的一天,从本质上说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不小心在梦境中沦陷了罢了。
但是这是从现实来看实在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实在界看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本质上都是坏人,我们只不过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沐猴而冠,把自己装扮出一副好人的样子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康掉转了现实和梦境谁更加反映人的本质这个问题,认为是反映了真实之欲望的梦境更加能够代表人的本质。季广茂在这里举了个对于中国人更加友好的例子,在《狂人日记》中,主人公只有疯了才能清醒地意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但一旦治愈了,就欣欣然加入了吃人的队伍里去。
实在界的知识
实在界的知识性质特殊,受到了意识的压抑和理性的过滤,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还有这种“知”。我们并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究竟知道了多少,因为这种无法融入符号秩序的创伤性时间总是被我们刻意去压抑了的,就好像是“给我一杯忘情水”一样。
但是被压抑不代表被彻底遗忘,被压抑之物总要用各种方式回归。
无所知
只有在不知道或者是误认的情况下,无意识之创伤才能呈现出来。如果我们一味直面现实,直面实在界与创伤性世界,它们或许就被深深压抑了。而我们一旦知情太多,过于接近无意识之真相,有可能“自我”会崩解。
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就在于获知了自己弑父娶母的无意识之知,他的自我就自行消解,这个时候他就只能摸出自己的符号身份,把自己流放。
主体想要维持自己的“自我”,就必须压抑被社会所不容许的不法欲望,必须对自己的不法欲望有所不知,把它们排除在自己的“意识之知”以外。主体想要保持自己的一致性,必须以某种“无所知”作为前提。这些必须保持“无所知”状态的东西,绝对不能道破。
实在界之应答
实在界虽然总是以创伤性回归的方式爆发,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但是实在界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支撑。
齐泽克举了一个例子,《太阳帝国》(哦,为数不多我看过的)里面,小男孩在宾馆的窗子上对着上海外面的日军战舰打了打手电,结果日军的炮弹呼啸着就飞了过来。季广茂也举了个例子,说单位里面有个老领导,戒了几次烟,结果每次都正好戒着呢,单位里面总是正好出了乱七八糟的岔子,意外搞死人。于是小男孩觉得太平洋战争导火索竟是我自己,我实数东亚带恶人;老领导觉得哎呀冥冥中自有天意,是老天不想让我戒烟的。
这里我们发现,其实这些情况,看似是应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凑巧。只不过这种凑巧实在是过于离谱,以至于完全动摇了我们的现实感(实在界的入侵)。面对着这种现实感的丧失,人产生了一种应激性的倒错,把自己的无能给倒置为了无所不能(为实在界的入侵承担全部罪责)。我们不难发现,上文小男孩把日本战舰炮击上海视作是自己所作所为的恶果,这已经可以说是狂妄自大到了离谱了——但是小男孩不得不这么做,必须要给它赋予一个意义,“那不然也太离谱了,做梦都不敢这么编”。
一小片实在界
实在界之应答实际上只是凑巧,但是这种凑巧开始了我们的阐释运动,意义实际上就是被这么阐释出来的。而现实中事物要产生意义,就得凭借这种实在界来支撑(有点像是逆练休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拉康就有“人和人的交流都是成功的误解”这个说法——我们以为对面用的符号系统和我们的是同一套,我们嘴里的/píngguǒ/指的是同一个🍎,而事实上,这不也是一种凑巧的误解,这不也是一种实在界的应答吗?
有一则笑话说明这个问题:老师问学生:“学生在回答老师问题时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学生想了半天,说:“我不知道。”老师:“很好,谢谢!”
在这个笑话里,学生和老师的“我不知道”(能指)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所指),也就是说两个人在用两套不一样的符号系统交流。但是老师“以为”学生和他用的是一套符号系统,两个人的“我不知道”指的是同一个意思,这里其实就是一种凑巧的误解,一种实在界的应答了。这种纯属意外的“以为”就是“一小片实在界”(相对于日本战舰炮击上海确实够小了吧),没有这种“一小片实在界”的支撑,交流是进行不下去的。
四种话语
早期拉康信结构主义那一套,注重话语分析。他把所有的话语分成四种:主人话语、大学话语、癔症话语和精神分析师话语。
主人话语
主人话语中有一种“主人能指”,它能取代其他所有的能指,谈论所有的话语。主人能指能够“缝合”所有其他的能指。
比如说最经典的主任能指是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民主是号称消灭了阶级斗争的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女权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另类形式……一切可以被阶级斗争所解释。
大学话语
把主人话语制造出来的排泄物当做宝,转化为知识,硬灌输给尚未驯化的学生,将他们转化为主体。大学教师仿佛主人,学生仿佛奴隶。
癔症话语
癔症话语针对的是“符号性委任”。这里也有一个经典的笑话,“一个小丑以为自己是个国王,那他是疯子,一个国王以为自己真的是个国王,那他更是个疯子”。
精神分析师话语
分析师话语和主人话语正好相反。精神分析师话语出在客体的位置。(我没懂)
两次死亡
庸俗的理解就是肉体死亡和符号死亡。
有的人肉体已经死亡了,其符号价值却还有某种剩余,我们对于这样的人问心有愧,他们也会追逐我们,令我们魂牵梦萦,寝食难安。电影里复活的死人都是因为他们没能获得好好的安葬而死而复生,为的是追索未偿还的“符号性债务”(通俗的理解也就是一场葬礼),只有通过适当的符号化,将死者纳入符号系统中,他们才会安然死去。
他们的死亡是一种创伤性事件(实在界),必须要将之符号化,用适当的形式纳入历史记忆中,才能消解其创伤之维。
小客体 (object petit a)

可望不可即的欲望客体,欲望的客体-成因。
实在界在进入符号界之后,符号界无法消化而形成的残渣。 实在界总是要进入符号界的,但是又无法全部进入,总要产生某些残渣,这些残渣就是小客体。比如说我们都有创伤性经历,我们无法将之言说,也就无法将其符号化。但是我们必须将其符号化,化解内心的创伤,但是总有些东西是符号化剩下的,那就是小客体。
主人能指试图把所有的能指给缝合起来,但总是造成剩余,缝不进去,那就是小客体。
拉康晚年描述小客体的时候还会用“不可能的-实在界的”来表述其性质。这表明小客体属于实在界,并且主体与小客体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关系。主体永远不可能得到小客体,永远不可能与小客体建立直接的掌握与被掌握的关系。主体不可能得到欲望的客体-成因。
原质
任何客体都可以成为原质,只要它能占据原质的位置。要占据原质的位置,必须要占据一个幻觉——那个客体本来就是那里的,而不是因为偶然才被放在那里的。比如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里面的石人就是这么这样的原质,明明是人为埋进去的,却让人以为是天意。
崇高客体本来就是庸常客体,但是一不小心被提升成了原质,具有了原质才具有的尊严,于是成为崇高的客体。崇高客体笼罩在魅力中,一旦魅力烟消云散,剩下的就是一堆残渣,连普通客体都不如。“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大抵如此,本是鸡,一不留神,被置于凤凰的符号里,被赋予了凤凰的“符号性委任”,成了凤凰;但是它一旦被逐出那个凤凰的符号,就只是鸡的残余,也就不如鸡了。
大他者
拉康的大他者并不赋予任何事物以结构,反而赋予任何事物以纯粹的偶然性。大他者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说黑格尔的“历史的理性”、亚当斯密“看不见的大手”都是如此。
大他者是偶然性的,但是它拼命掩盖自己的偶然性。我们只有顺从于它, 才能保证完整的现实感。就比如说爸爸带着儿子去朋友家,朋友有事出去了一会,这个时候里他家的热水瓶自己爆掉了。实际上这个热水瓶爆掉就是纯粹的偶然,但是为了不让朋友以为他家是会为了小事而说谎的人(“平时都没事,怎么就你们家来的时候坏了?”这是为了维持符号系统的一致性),他们自己背了黑锅,承认是自己不小心弄爆的(牺牲真相,自己承担责任)。
大他者的力量来自与其凝视。即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欲望与驱力
欲望是全局的,驱力是局部的。
欲望讲究辩证法,绕来绕去。驱力一往无前,直来直去,不讲辩证。
Desire = Demand - Need
Need是不需要被设置的, 因为总是与生俱来就被预先设置好了,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这个总不可能还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但是一旦need被放在符号网络里面,need需要就会转化为demand要求,就要对大他者提出呼唤。婴儿向母亲要奶,一开始只是为了解饿,但是后来就变得不再只是为了解饿,他会想要某种比起解饿而言更多的东西,这个就是demand,这多出来的部分就是desire——他欲求母亲之爱。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need需求满足的只是使用价值,而demand要求则满足交换价值。
这就带来一个推论,一个物品本来只是再寻常不过的物品,一旦被纳入符号体系,赋予这个物品本不具有的符号价值,就会导致欲望的形成。消费名牌意味着获得了大他者之认可,意味着符号的增殖,也就意味着交换价值对于使用价值的扬弃。
欲望的辩证法
欲望永远围绕着客体-成因(对象a)做循环运动,就和乌洛波洛斯之蛇一样,但是欲望本身却对这一运动浑然不知。
欲望之为欲望,在于欲望一直推迟自己的满足,在于推迟、拖延、犹豫不决。本质上,欲望永远都是未完成的,总是未被满足的。
欲望总是在自我增殖,这种增殖也就是匮乏的增殖,而匮乏也就是欲望之为欲望的根本。
欲望的反面是焦虑,这种焦虑不是因为无法抵达所欲之物,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太过接近欲望的成因-客体,以至于失去了匮乏,部分地满足了欲望,这也就带来了欲望的消失。
幻象空间
符号空间有符号律令或符号委任,具有普遍性;幻象空间则是个人活着团体组织自身快感的方式,是绝对特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幻象空间虽然涉及想象界,但是与实在界更为密切。
有些人物总在幻象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说所谓红颜多薄命,不仅是经验的,在幻想空间层面上也是如此,因为她只有薄命,才能永远活在我们的幻象之中。真正的爱情永远、必定、必须是夭折的,不夭折的都走进坟墓了。泰坦尼克号为什么要撞冰山,要是不撞上冰山,那高贵小姐和底层臭小子一起生活这种事情比起大船撞冰山还要离谱,那还不如撞了,那萝丝还能永远在想象中幻象“如果当年没有撞上冰山那么我和杰克可以永远幸福”。
幻象空间的另一功能是掩盖创伤和失败,是一种替代性的弥补。“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忧”实际上是掩饰自己的忧虑。有些人喜欢做媒,实际上是掩饰自己婚姻爱情的失败。
征候 (sinthome)
拉康有两个词,一个是征候(sinthome),还有一个是征兆(symptome),拉康和齐泽克有时候都会混用这两个词,甚至征候那个词就是征兆这个词的法语古体字拼法。
早期拉康只有征兆这么一个词,是语言学上拿来的,把征兆视作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加密的能指。
后来他用的征候,则指的是快感之核。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快感之核。驱力的不断重复和自我复制也会导致快感。瞎鸡巴反复的纯粹能指,不包含任何所指,充满了愚蠢的快感,这也就是征候。征候不包含信息、意义、价值,就只是无意义的字符。
季广茂举了聊斋里面《抽肠》作为例子,来说明这种前语言的纯粹快感。那小说我读着渗人,就不复制了。